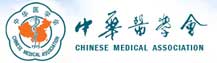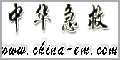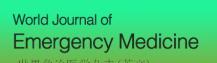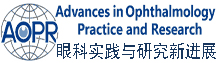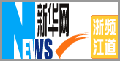| 现在位置是: | 首 页 | >> |
 | 关键字: |
In the Shadow of Copper: A Volunteer’s Tale of Tenderness and Resilience
作者:周朱瑛,蒋春明,缪玮彤
发布日期:2025-09-09
周朱瑛,蒋春明,缪玮彤. 铜墙铁壁中的温情[J].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, 2025,34 (9):1257-1257.
铜墙铁壁中的温情
在医院的志愿者服务中,我见证了许多生命的脆弱与坚韧,但小勇的故事,始终让我久久难以忘怀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故事,更是一段充满爱与希望的旅程。
记得那天刚进入儿科门诊单元,我们经验老道的分诊护士婷姐就叮嘱我:“彤彤,多关注下小勇这孩子,这个孩子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闭症。”我点点头。
“小勇,你好,我是这里的志愿者姐姐,你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,叫我彤彤姐姐哦。”可7岁的小勇好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,眼神始终低垂着,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金属扶手,“咚咚”声像一把钝刀,划破诊室的宁静。
小勇爷爷佝偻着背站在一旁,手里拎着一个放胶片的塑料袋,袋子里除了胶片还有一叠厚厚的病历,“医生,您别介意啊,这孩子就这样,不爱搭理人。诶,孩子命苦啊……”老人声音沙哑地说道,又像是在喃喃自语。
我摆摆手:“爷爷,不要紧的。”
我蹲下来,从笔记本撕下一页纸,折了只纸飞机,试探着和小勇说道:“小勇,你看,飞机要飞喽,来,你也来玩一下吧?”他突然停下了敲击,抓住纸飞机往地上重重一扔,纸片散开。
爷爷训斥了小勇几句,皱着眉头、不好意思地和我说道:“医生啊,他现在就这样,不爱玩玩具,也不和别人玩,诶,一点儿教不起来。在老家,光康复就花了不少钱,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,反而越来越差。诶,现在他爸妈也不管他了,我是实在看不下去,也想不明白,小时候看着还挺机灵的孩子,怎么越大越不一样了?过年时和我女儿说起这事儿,哦,就是小勇他姑姑,她说要么带来杭州看看,我想着可别再耽搁了,就赶紧过来了。”
爷爷的脸上布满了苦楚与无奈,我心中五味杂陈,也瞬间恍然大悟——怪不得刚进来时,婷姐便特意叮嘱我要多留意小勇。回想起以往接触过的自闭症孩子,他们大多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些端倪了:要么眼神游离,难以与人对视,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;要么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,对外界的声音指令充耳不闻;又或是行为举止间透着与同龄孩子截然不同的刻板与重复。
然而,小勇的情况却不一样。爷爷说,小勇小时候也曾是个活泼可爱、眼神灵动的孩子,可谁曾想,随着年龄的增长,小勇渐渐出现了这些令人揪心的变化。病初,小勇的父母也着急,他们四处奔波,带着孩子辗转于各大医院。治疗和康复的费用本就不低,对于一个本就生活拮据的农村家庭而言,这其中的艰难困苦,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道尽的?
更令人唏嘘的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勇的病情似乎并未如他们所愿那般好转,生活的重压与无尽的绝望渐渐磨灭了父母的耐心与希望,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,将这份沉重的责任都留给了年迈的爷爷。而爷爷,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却依然坚守着那份对孙儿深深的爱与不舍,用爷爷自己的话说是,“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,咱们也要试一试”。爷爷的这份爱与坚持,怎能不让人动容,又怎能不让人感叹生活的不易与亲情的伟大呢?
我又折了只青蛙:“小勇,那这次我们试着让它跳好不好?”小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,有点儿疼,但我没抽手,他愣了愣,松开手,把青蛙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。
终于轮到小勇了,一进门,爷爷就焦急地向主任问到:“主任,孩子他到底是怎么了?还能治好吗?”
主任仔细地观察着小勇,又看了看孩子的手心,问到“孩子的皮肤一直是这么黄的吗?”
“主任,孩子小时候也是白嫩的,这几年才这么黑黄的”爷爷说道。
“嗯,好的,先给孩子做个化验,查下肝功能吧。”主任快速地在电脑上开出相关化验单。
“漫长”的一个小时之后化验结果出来了,正如主任所预判的那样,小勇的肝功能有异常,这个发现如同一束微光,隐隐透露出小勇或许并非是单纯的自闭症。爷爷攥着那张化验单,手指微微颤抖,他害怕这未知的异常会为小勇带来更多的病痛折磨;然而他也明白,或许这也是治好小勇的关键线索。
此时主任察觉到了小勇爷爷内心的波澜,他轻轻拍了拍老人的肩膀,温和而坚定地说道:“孩子爷爷,别太担心,先让小勇住进病房吧。接下来,我们会为他安排全面的检查,等诊断结果更加明确之后,我们再根据小勇的具体情况,量身定制一套最适合他的治疗方案。”
进入病房之后,小勇一边进行护肝治疗,一边完成其他检查。要完成检查,对于小勇来说并非易事,他像一只受惊的小鸟,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抗拒与不安,经常发脾气、不配合。我陪着爷爷和小勇在各个辅助科室里穿梭,看着爷爷焦急、无奈又心疼的眼神,我的心也紧紧地揪了起来,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攥住。
幸亏我不是孤身一人,之前的志愿者经历让我和辅助科室的医生们很熟悉了,每次去一个特检科室之前,我都会提前和他们介绍一下小勇的情况,而医生们得知小勇的特殊情况后,也总是会给予他特别的关怀与照顾。他们会特意为小勇留出足够宽裕的时间,让他能够慢慢地适应检查的环境,缓解内心的紧张与害怕。那一句句温柔的话语、那一个个鼓励的眼神,就像冬日里的暖阳,温暖着小勇和爷爷。
在这段时间里,我发现小勇其实能明白很多事,只是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我尝试着用简单的手势和表情与他交流,慢慢地,他开始对我露出了一些笑容,有时候他甚至会突然开心地跳到我跟前。
一周后,小勇的结果陆陆续续出来一部分,“血肝功能异常,铜蓝蛋白低,尿铜高……”主任的笔尖在化验单上重重一划,“是肝豆状核变性,一种铜代谢障碍的遗传病。ATP7B基因的检测结果还没这么快出来,但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。”
病房里安静了下来,爷爷张了张嘴,浑浊的眼里泛起水光:“铜……是啥?能治吗?”
主任拍拍爷爷的手,耐心地解释道“小勇爷爷啊,咱们每个人身体里都得有点铜,就像炒菜得放盐一样,少了不行。可小勇这孩子啊,就像家里的下水道堵住了,铜排不出去,全堵在肝脏和脑袋瓜子里头了。这肝豆状核变性啊,就是铜把肝脏当成了"铜墙铁壁",把大脑当成了"铜皮铁桶",到处捣乱。所以您总说孩子小时后还机灵,越大越不一样了,还有孩子的肝酶也升高了,这都是铜排不出去,在身体里捣的鬼。”
“主任,那咋办?能把孩子身体里的铜排出去吗?”爷爷焦急地问道。
“对,小勇爷爷,您问得很对,接下来,咱们就是得想办法把多余的铜给排出去!让孩子的肝脏和大脑变得干干净净。”
“好的,好的,谢谢主任,谢谢医生,谢谢!”沧桑的老人此时激动得不停地道谢。
第二天清晨,我走进病房时,看见小勇爷爷正在向家里打电话:“老太婆,咱们小勇不是傻子,是病了!治得好的!诶,就是小勇不愿意吃药,吃个药,就跟要了他的命一样。”
爷爷说这已经是小勇第三次把青霉胺药片吐出来了,他的嘴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。见状,我变术法似的掏出口袋里的彩虹糖:“小勇,你看这么多糖,很好吃的。一会儿啊你把这个药吞下去,姐姐就奖励你一颗。”他盯着不同颜色的糖看了很久,最后一闭眼睛,咕咚一下吞下药片,然后快速地从我手上拿走一颗紫色的糖果,放入嘴里。见状,我和爷爷相视一笑。
病房窗台积灰的拼图盒里,总是少那么最后的几块碎片。所以我自己买了一套星空拼图,那是小勇第一次主动挨着我坐下,我们慢慢拼着,直到拼到最后一颗星星,他突然抓起一块塞给我:“啊!啊!”我高兴地接过、拼上、填满。那天,我听见爷爷又在走廊打电话:“老太婆,咱们小勇会分东西给人了……真的,没哄你……”
治疗的日子里,虽然小勇进步得很慢,但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让我感到无比欣慰。我看到他在努力地跟着康复师学习说话,努力地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我知道,他也在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努力。主任说,驱铜治疗若能坚持,小勇或许能有很大的进步。出院那天,小勇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不愿松开。我笑了笑,接着便把自己带在身上的星形徽章拿出来别在他衣服上。“一定要加油好起来哦小勇”我轻轻地揉着他的头发。
几个月后,回访时,姑姑给我们发来一段视频:小勇蹲在老家的泥地上,和小伙伴在玩泥巴。阳光落在他发梢上,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。镜头外传来了小勇爷爷的声音“主任、彤彤医生,小勇现在知道和孩子们玩了。下个月啊,我就带他来杭州看你们。”
小勇的故事,是一面镜子,映照着医疗体系中对“非常态”的迟钝,也映照出亲情的韧性与微光。当铜锈褪去,留下的不应仅是庆幸,更应是警醒。在标准与效率至上的时代,我们是否遗落了那些“不典型”的生命?或许医学的慈悲,不仅在于药石,更在于愿意为那些“异常”的生命,多停留一刻的目光。
当初报名志愿者时,我以为自己只是来“陪伴”。可当小勇学会用糖的颜色表达情绪,当他把最后一颗蓝色拼图分给我时——我突然懂了主任那句话:“有些孩子不是不会发光,只是需要有人帮他们擦亮火柴。”
DOI号:10.3760/cma.j.cn114656-20250416-00296
基金项目:浙江中医药大学2024年教学学术研究项目(BXS24005)
关键词: